这些家长也是历史与生活的受害者,“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本文由ONE实验室原创。首发于「ONE·一个App」。触乐获得授权转载。
ONE实验室是一个致力于非虚构故事与报道工作的新创机构,为“ONE·一个”媒体群供稿。ONE实验室所发表作品均经事实核查。
导语:这位母亲把就读于清华美院的儿子骗入临沂市网戒中心,又发现了网戒中心的阴暗,在那里展开对于儿子的争夺大战。这是一个爱沦为权力、控制,亲密关系逐步损坏却修复无能的故事,正如她儿子王一南所说,“这一代家长他们自己需要成长,才配收获亲子之间修复的关系”。这也是关于一个女人的真实生活与她的理想世界的故事。如果这些家长是网戒中心得以存在的“帮凶”,那么他们也是历史与生活的受害者,“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 把儿子骗进网戒中心
把儿子王一南骗进临沂市网戒中心的8年后,邹虹认错了,甚至屈从了,儿子带有胁迫意味地建议她接受ONE实验室的采访,她就接受了。但是她与儿子之间从未达成真正的一致。儿子将她划入杨永信、网戒中心一方——加害者阵营,邹虹多少有些委屈,觉得当年情非得已,不慎受骗,也是受害者,争吵时她也不忘提醒儿子,“我还在那里为你作斗争呢!”采访中她讲了第一个故事,以表明心迹——儿子是她的信仰,生命意义的归宿,她为儿子做的一切因此都具备了牺牲、忍耐、崇高的色彩——故事来源模糊,一位视贞洁如生命的母亲被强奸后本想自杀,可为了儿子,选择忍辱负重活下去。“你的孩子才是天呢!我欣赏是这样的价值观。”
邹虹把采访地点定在了北京的一家褡裢火烧店。她60岁,是银行退休职员,挑染成栗色的头发略微花白,身材不高,但总像提着一股气似的,挺胸抬头。她埋头看着手上摊开的一个塑料皮面的小本,上面记着计划中的谈话要点。在我问问题之前,她先是以受害者母亲的身份斥责了一通网戒中心。她说出的事实少,观点多,激动时顾自对着空气指指戳戳,争辩、指责——仿佛她的斗争对象近在眼前。她有时无视提问,反而盘问起我来,仿佛也是我的严厉家长。她关心我为何选他儿子采访,“他什么引起你注意了?”急切地想弄清儿子对她的最新评价,“后来我做的工作什么的怎么样,他提到了?他怎么提的?”
尽管我尽量挑选王一南的评价中最温和的部分转述给她,她还是相当失望,“还纠结呢?那他也是够傻的。”她叹了口气,“当时给他送去,这点他一直是仇恨在心的。”
邹虹这样一个人是不会随便把儿子交给一个陌生机构的。送王一南进网戒中心之前,她提前去考察了大半天,看看环境、吃住如何。医生们笑容满面,孩子都说好,家长也说来吧,共患难。没有玩电脑的环境了,课堂上讲着《弟子规》,孩子们天天早起跑步,“都像个人似的”。网戒中心通过了她的初步考核。
王一南那时在清华美院读大一,沉迷《魔兽世界》,一天打十几个小时,挂科大半,“不是正常人的活法”,邹虹生怕儿子“玩着玩着磕死在电脑上”。2008年大年夜,她关好了家里的煤气,带上几床被子,骗儿子说去山东走亲戚,跟丈夫一起开车把他送进了网戒中心,寄希望于在不久的将来,收获一个崭新的儿子。
发现被骗后,王一南咒骂、绝食、挣扎,直到被摁在了十三号室的床上,遭到电击。一个小时后,他开始改口、求饶。出来后见到邹虹,他委屈又恐惧,不敢提电击,没给她看手心上灼烧出来的密集小红点,没告诉她自己是怎么被绑着、怎么被电、怎么被恐吓着承认有网瘾。“我跟我妈就已经没有任何信任了在当时。”
从十三号室出来后,他被强制参与集体活动——观看春晚。晚上,他不敢仰面朝天地睡,这个姿势让他条件反射般想起那个房间里的情形,只能侧着、趴着,惊恐难眠。
邹虹不知道这些,十三号室对于外面的家长来说,就像一口沉默的深井。谈论这个房间是被禁止的,旁观“治疗”也不被允许。可看到儿子畏畏缩缩,不敢说话,只是哭,邹虹起了疑心。她问别的家长十三号室里到底怎么电孩子,其中一位说自己查书了,没有任何副作用。更多的家长一无所知。
“傻,是真傻”,邹虹为他们着急。她目睹过一个新来的孩子出来后拼命挣扎,“就跟杀猪似的”,间接地感到事态严重。
她去问网戒中心的医生,医生说是低剂量,不痛苦。她要求亲自体验体验,“孩子能受,我怎么受不了?”医生拒绝,她当即说她儿子“不弄”,不接受不甚明了的治疗。
邹虹对十三号室执着的调查,儿子对此毫不领情。“我不认可她对电击的好奇心”,王一南在措辞中把母亲的忧虑和关爱降格为“好奇心”。在后来8年数不清的争吵中,他曾跟她建议,“你自己电一下吧,你自己试试,再跟我说怎么怎么回事儿。”于是,她买了一台低频电子治疗仪,在家自己电自己——没试出结果,强度、机器台数、针插在何处,造成的疼痛差别巨大。她只能想象儿子遭受的痛苦,并被这种想象所折磨。

■ 权力回收
一天中午,有人传话说王一南犯病了,邹虹立刻冲了出去。儿子蹲在地上,被一些家长和盟友围在中间,因忍受着极大痛苦发出呻吟。有家长说这孩子八成装病,医生拿着听诊器听来听去,没有结论。邹虹心思都在儿子身上,王一南小时候就犯这种怪病,紧张、长时间憋尿会导致身体痉挛,跟肚子抽筋儿似的,蹲在地上动弹不得,大腿根紧贴肚皮才能缓解一丁点儿。X光、胃镜都做了,没查出原因。这病一发作就是好几个小时。
当天晚上她去找医生理论,医生推脱给家委会,后者是网戒中心名义上的管理者。在入院时,所有家长都要跟“家长委员会”签订协议,“相信、坚持、配合”治疗和管理。邹虹不打算相信、坚持、配合了。尤其是那些跟治网瘾毫无关系的规定,比如每个孩子早上只能上一次厕所,完全是出于管理方便。她向家委会据理力争,规定取消了。她进一步提出要求,从今往后,不经她本人允许,她儿子不进十三号室,同时也不吃药,也不打针了。家委会模糊地答应“给予关照”。
邹虹事后懊悔当时没谈透。几天后的傍晚她买饭回来,发现儿子又被弄进去了。出来时,他扑在她身上就哭。她认定他们在报复。她气急败坏,跑去把家委会办公室的门拍得“咣咣”响。对方说在开会,稍后谈。她嚷嚷起来,“我这事儿大,要不开门,谁他妈也甭想过。”
她不依不饶,充满斗志,扯着嗓子要求把儿子的一切权利交还到她这个母亲的手里。“意见不一致,说着说着就声儿高了嘛。他高了,我也高了,谁怕谁啊。反正我豁出去了。”
家委会代表让了一步,答应放权3天。邹虹说不行,对方又说7天。她仍不答应,挨个谈话,逼着几个家委和医生点头答应,不再让她儿子进十三号室。 “就敲死了。”她认为自己控制住了局面,“管事的反正都答应了”。
一周以后,家委会试图回收临时下放的权力,邹虹则一次次搪塞说还没考虑好。各种人来做她的思想工作,软硬兼施,而她软硬不吃。“我怕谁啊,我这个性格就不是一小女人的性格。”邹虹说。
有一次,邹虹要回北京办事,为了让儿子安心,她挨个去找医生、家委谈,让他们保证不把她儿子弄进十三号室。他们表态后,她宣布这些话她全录音了。王一南父亲留下陪伴儿子,她不放心,叮嘱说孩子的事情她说了算。她觉得他父亲顶不住压力,“他爸爸太好对付了。”她警告院方,“我不在的时候谁要敢把一南弄进去,我要加倍地惩罚你们。”

■ 对抗杨永信
邹虹特立独行,坏了网戒中心不少规矩。新来一个孩子,从十三号室里出来大闹,家长犹豫要不要在这治。别的家长都帮着劝留,她却偷偷跟那家长说,他家孩子不适合,这里很残酷。家长带着孩子走了。
邹虹给人一种印象,像在马路上逆行的人,她总是能找到斗争对象和目标。比如对于“雷某”案,她也很激愤,只不过似是而非地归因为“司法腐败”。她看不惯杨永信对名声的贪恋,“你看他满屋子都是锦旗啊什么的,他拿这当回事儿”。网戒中心安排记者采访,她不愿她名牌大学的儿子成为宣传素材,一概拒绝。为了躲避镜头,她还蒙了个口罩在脸上。儿子出院时,她无视惯例,没送锦旗。
“发展客户”她也不干。每个家长都被施了压——受益了要感恩,最好的感恩方式是让别的孩子也受益。隔三差五地,点评师们会在课堂上盘点,“已经做过工作的举手”,“一个都没成功介绍的举手”,邹虹总是惹人注目地位列其中。
点评师们说先让人来最要紧,来了再解释电击这些治疗方法。邹虹不认可这做派,不光明正大,带点儿忽悠人的意思。她拒绝介绍,“业绩”保持为零。
网戒中心倡导下跪,孩子跪家长、跪“杨叔”,家长出于感激也跪“杨叔”。邹虹看不惯这风气,她教育儿子要有骨气,别动不动下跪。
一天,点评课上一边放着《羔羊跪乳》《烛光里的妈妈》之类倡导孝道的视频,王一南母子等人被点了名,站到教室中央。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和引导后,一个“盟友”率先大喊“儿子不孝”,扑通跪下,哇哇大哭起来。其他盟友也纷纷效仿起来。家长们看起来都很受感动。邹虹觉得没到那地步,要她演也演不出来,最多配合着拉拉手、拍拍肩,就尽量让儿子跟她靠边站,“就我们俩在站着,多不合适。”
邹虹回北京期间,中青报发表了曝光网戒中心的报道。家委会认定这事是她闹的,她有这样的能量。邹虹懒得解释,“当时就出我这么一个另类,”她明白杨永信对她不满,她破坏了他的规矩,“他脸上无光了”。
杨永信没像驱赶别的不服从者一样让他们母子离院。“我的名牌大学身份就像妖怪眼中的唐僧肉,让杨永信垂涎”,王一南说。邹虹认为这也是因为杨傲慢轻敌,深信最终能拿下他们母子。在疗程即将满期的一天,杨永信在课堂上点了王一南的名。邹虹和儿子一起站到了500平米课堂中央,接受两侧四百来个家长和盟友的注视。
杨永信欲抑先扬,夸了一顿“王一南妈妈”教育出高材生儿子。接着话锋一转,说她儿子沉迷网络说明她不会做母亲,既然来了,就该跟大家一样。“你儿子这样,你看他有进步吗?王一南妈妈是聪明人嘛,明白了吧?把孩子交出来。”
曾有家长也试图夺权,但经过杨永信在大会上的施压后,退让了,说交给杨叔。“既然XXX妈妈明白了,王一南的妈妈也会明白的。”杨永信发号施令,“我们给她鼓掌。”两人被掌声包围。
杨永信见她岿然不动,又让别的家长和“盟友”谈王一南现象。有家长便说你的孩子没养好,说明你水平不够,大家保持一致多好。也有小孩领会意图站起来说,“阿姨,你让一南跟我们一样吧,相信杨叔一定把他能弄好。”
发言完毕,杨永信号召了新一轮掌声,“王一南妈妈还糊涂着,我们再给她机会。”在反复的掌声和反复的表态要求中,她只是一遍一遍地回答,“我孩子,我心里有数。” “当时的想法就是死磕。你夸我,也他妈放屁,你骂我,也放屁,无所谓。”邹虹回忆说。
直到午饭时间,杨永信仍捱着不下课。“大家都因为你们母子俩没法吃饭。”邹虹想,一起饿着呗,不怕。她很坦然,我没让大家不吃饭,是杨永信不许吃饭。
看邹虹磕不动,杨永信转向王一南,“你表个态。”王一南仗着母亲撑腰,表态说,“我听我妈的。”
15岁的徐浩坐在下面,看着邹虹长时间、孤零零地站着,忍受一轮轮的掌声,被感动了。“我觉得特别伟大。”他多希望在场的母亲也能像王一南妈妈那样挺身而出。可她却跟其他家长一样昏昏沉沉,举报他时却毫不手软。有一次,别人悔悟痛哭时,他装模作样地挤眼泪,便被她举报“感悟不深”,因此进了十三号室。王一南总共才被电3次,而他光是最多的一天就被电了4次。“我要有这样一位母亲就好了。”徐浩说。
杨永信号召了一轮又一轮掌声,邹虹只好一分一秒地捱着。如今她已经忘记掌声是如何熄灭的,只记得这样的场面后来也重演过两三次,她有一种“这事儿永远没完”的感觉,却始终像战士抵御洪水那样,抵御住了掌声,紧紧守着儿子,让他免于电击。
“他最后也没拿下。”邹虹笑了。

■ 认知分歧
跟杨永信对峙时,邹虹没怎么注意到儿子。“没什么反应,”她努力回忆。但她猜测他应该挺高兴的。
“我其实没有什么高兴的,”王一南驳斥了他母亲的想象力。“她老觉得这事儿好像是她的功劳似的。”他提醒她,正是她把他送到这样一个“特别卑鄙的地方”,此事由她而起,她随时可以终止,但她没有。她的说法是,害怕儿子离院后又钻回游戏里,“利用那隔离一下。”
在很多事情上,邹虹都和儿子产生了认知分歧,有时他们的理解截然相反。她感到困窘,不知所措,就好像儿子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在对她讲话。
对峙事件在邹虹的记忆中算是成就一桩。作为母亲,她挺住了,没有任人宰割,保护了儿子。因此回忆时,她带着称职母亲拥有的骄傲神色。但儿子毫不感激。他反问,不被强制难道不是一个成年人本该有的权利?
王一南早就明白,他、母亲、院方是三方不同利益。他,为了自己的安全生存;他母亲,为了“所谓的照顾儿子,所谓的帮助儿子”;院方,“为了那些勾当”。他在几年后才告诉她,他当时是装病骗她的,演得那么卖力,不过为了激她去跟他们斗争。邹虹觉得很意外,抱怨儿子隐瞒她这么多年。
王一南还故意吃素,严格持续一整年。在网戒中心,清水煮白菜豆腐,叫吃特餐,专治挑食,是杨永信发明的戒网程序的108个环节之一。他主动要求吃特餐,邹虹束手无策地眼看着儿子把肉汤里能看到的肉末都一点一点挑出来,搁在废纸上。有家长建议她求助杨叔来治,她没好气地说,“是,十三号室出来,让他吃屎,肯定都能吃。”她至今以为儿子是受了什么刺激,没想过这是对她过错的提醒。
出院后的年夜饭桌上,邹虹给儿子夹肉时,立刻被他扔回她碗里。他正是前一年除夕被送进网戒中心的,阖家欢乐的气氛让他回忆起被电击后强制看春晚的情形,他感到恐惧和恶心。他希望她羞愧,意识到自己做母亲的失败,但不确定她有没有接收到以上信号。
认知分歧从王一南小时候就开始了。那时他还会把自己的画分享给母亲看。他在初二数学课上打盹儿,半睡半醒之间,脑子里突然出现了美妙线条,他迫不及待画在笔记本上。回家捧给母亲看,她应付着说“挺好”,却没有分辨出那是一只猫。起初他只是隐约感觉这是一种审美上的隔阂。12岁那年,他在一次全球少儿奥运绘画比赛中得了奖,父母和他都被邀请去悉尼看奥运会,萨马兰奇亲自给他颁了奖。人们叫他“奥运小画家”。他蔫蔫儿的,不知道怎么答记者问。母亲从那时起就爱代他回答,“他为国争光,可激动了”,没考虑到这根本不是她儿子的想法。
王一南觉得母亲似乎很享受他的荣誉头衔。她替儿子接待记者、安排活动,把他得奖的画印成贺年卡四处寄。她为他整理作品集,把报道从报纸上剪下来,装订成一本。“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我妈妈的作品集。”王一南说。她逢人就展示,没意识到儿子为此尴尬,“我觉得她跟发小广告似的”。
一次在王府井逛街,邹虹看到儿子的得奖作品被贴在一家麦当劳的玻璃上,当即让儿子过去“照一个”。她觉得这是一个无比难得的纪念,何况是王府井这么重要的地方,于是下达了“必须照”的指令。儿子犟了起来。最后,王一南被母亲拧着耳朵,哭着跟自己的获奖作品拍了合影。
儿子的指责让邹虹感到委屈,她觉得他也从这些荣誉中受益了,很伤感地批评他,“太自我了,缺少感恩,缺少体贴。”她度过了不争不抢甚至不求晋升的平凡人生,“我走的是那条追求名利的路吗?我发自内心不喜欢庸俗的生活。”
“我小时候真的,在里面挺挣扎的。”王一南感到他母亲有一个目的,完全不符合他的感受,却硬要把他包含其中。
初中他看《苏菲的世界》、《从一到无穷大》,脑子里飞着无数问题。他问邹虹,国家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爱它?闭上眼睛,世界还存不存在?母亲总是说出不容反驳的答案,诸如出生在这个国家,你就得爱它;世界肯定是唯物的等等。他觉得没意思,不想再跟她多交流了。邹虹在二十多年后依然委屈难忍,她已经尽力去回应敏感、早慧的儿子了,但他求知欲太过旺盛,半夜三点还缠着她问问题,“不让妈妈睡觉。”她也没有接受很高的教育,她还有自己的工作和烦恼,她很疲惫,应付不来。
后来王一南度过了“自我意识伸张得比较明确”的青春期,逐渐放弃了和母亲的交流。对女孩有模模糊糊的好感,他也不敢写在日记里(母亲曾翻出他写的日子,批评他写班主任的坏话),只写些意义不明的诗或者画意象不具体的画代替,排解单相思。到了高中,课上得没劲,他就翘课去网吧,沉迷在游戏中,那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脱离游戏很自然——母亲帮他探路、找名师开小灶,确立了考清华美院艺术史的目标。母子俩目标统一了,他自觉自愿地封了游戏账号。
考入清华美院后,他很快发现那不是个纯粹的艺术世界。同学们琢磨的事情多是户口、入党、就业之类的。他自己是北京人,家境良好,没有这个焦虑。课程不能满足他的胃口,同道的朋友极少,他感到孤独。
他又回到了游戏世界,越打越凶,停不下来,每天必须玩十几个小时,吃饭、上厕所时间都为此压缩。父母来宿舍看他,他也接着打。他也不是故意的,只是正打着呢——“没法跟团长请假。”
他知道,对于母亲来说,最不能接受的是两人无话可说,“我跟游戏里的人更能沟通。她就会觉得你对她很陌生,她不知道怎么融入你的心里,她就会产生恐惧、产生敌对,觉得你是有病,她就要治你。”他说。邹虹如今也有诚恳的反思,“因为亲密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孩子有网瘾。”
母亲的反对徒增他反抗的快乐。小时候,为了防止他打电脑游戏,母亲会藏鼠标。他就改玩键盘操作的游戏。《超级玛丽》无聊透了,“但是我就这么干,我就不服”。
这一回,王一南面对被大学劝退的危险。邹虹帮儿子办了休学,给他失控的生活踩了急刹车。她开始想各种辙,解决问题。她推理儿子的生活可能太单调了,就组织家人“农家乐”,或者请个老师谈话开导,显然没用。在网戒中心,网络游戏是所有家长憎恶的对象、共同的敌人。“最后就选了杨永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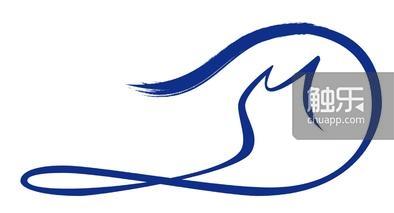

■ “赎罪”之路
2012年,王一南到意大利读书。他说不清楚为什么“陈年往事”又翻腾起来。每到阖家团圆的日子,或者看到军装、铁窗之类,他就陷入抑郁。他告诉邹虹,临沂那档事儿还没完。
王一南在采访中极少提到父亲。在网戒中心这件事情上,矛盾双方主要是他和母亲。“我妈挑的头,我爸就稀里糊涂的,”与父亲的矛盾是次要的,就像他在家庭中的位置、像他在儿子成长中扮演的角色一样次要。父亲有一次试图调停母子之间的战争,想找他谈谈临沂。气头上的王一南一句话就让他沉默了——“也少不了你。”父亲一度还帮着网戒中心编辑宣传材料。
有三个月时间他完全不理邹虹。去年,邹虹被他正式告知,如果不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他考虑以后不回国了。28年来,儿子一直是邹虹生活的核心。她退让了,问他怎么才能满意。
王一南郑重其事地提了5个条件:一、将相关罪魁祸首,杨永信和刘明银(邹虹正是参考了后者拍的电视纪录片《战网魔》把他送了进去))绳之以法;二、以其它途径“解决”上述二人(“虽不是我的本意,但临沂本身就不合法”);三、努力“运作”,动员社会力量使网戒中心关闭;四、劝说执迷不悟的家长,“给人家长整明白了”;五、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到让我满意的解决方案。
邹虹答应儿子,“我去努力,我尽量做到。”
按照儿子提出的纲领,邹虹开始了“赎罪”之路。她咨询了律师,律师说这事儿费劲,举证难。她也觉得性价比低。就算去告,“能打出什么来?”她希望做更有建设性的事情。她把手机递给我,让我看一个商业计划书。最初,她想建一个正规的戒网机构,但力有不逮。现在,她认为应该搭建一个平台,网瘾孩子的“心灵的救助站”,把专业的心理学家、医生、营养学家等等都邀请来,帮孩子们驱除阴影,走向社会。
她援引了一个来源不明的千万级数字,说是中国网瘾少年的数量,忧心忡忡地说中国是一个重灾区。
邹虹谈起她即将起航的创业项目,充满热忱。她描摹的愿景中,这个平台将以一个猫咪咖啡馆的形式落地。主题的确立与她跟她儿子都是爱猫人士有关。这个咖啡厅承载着一个母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这里将开展有关身心成长、健康养生的沙龙,“全是正能量的”。这里将严格挑选食材,禁止转基因、可乐这种垃圾食品出现。把一切不好的隔离在外,就像她一直以来做的那样。“这是儿子留给我的功课。”邹虹说。(截至发稿时,邹虹发来消息说,猫咪咖啡馆已经初步开了起来,她充实地忙碌着。)
帮助网瘾孩子也是邹虹的赎罪之举。每当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一些励志的文章,她都群发给她认为需要一看的人,比如他儿子,比如王一南的同期盟友、23岁的徐浩,有时候我也收到几条。她自称征服过抑郁症,知道自爱自强有多重要。她主张宽容,最爱举的例子是曼德拉,“蹲了27年监狱,最后他吃饭,他还把监狱的那些打手们请过来。”反对自怜,像澳大利亚演说家力克·胡哲,生来没有四肢,“比你那受的伤害还残酷”。
她劝徐浩朝前看,争口气把今后活好,试图用自己的理解力引导他,“现在你还有一个月的生命,我说你怎么办?假如给你三天光明,咱们还做杨永信那事儿,跟他较劲?”
这话被她拿来劝她儿子时,王一南听到只是“恶心”。他质疑母亲,“还老操心人家的事儿,自己都整不清楚。”
母子俩甚至在一个简单的名词上也无法理解一致。去年夏天,按照王一南的要求,邹虹重回了一趟临沂,跟网戒中心“结账”。网戒中心承诺,只要家长对孩子状态不满,可随时强制其返院,因此离院时,家长们往往留下几千、一万块,以备未来之需。
邹虹成功结了账,拿回了三千多块钱。她跟儿子说,医生、护士都很客气、和颜悦色,她怎么能跟人吵起来?她打听了,网戒中心有了很多的变化,“治疗”据说是也要本人同意了。但究竟改到什么程度,她没在那儿待,也不好说。她确实拿回了一份永久出院证明,儿子该有安全感,该原谅她了。
但邹虹没彻底明白儿子所说的“结账”不仅仅是结经济账的意思,也不仅仅是那份证明,他期望她去讨伐网戒中心,表明势不两立的态度,那样才能跟她做回一家人。“我觉得她去了白去。”王一南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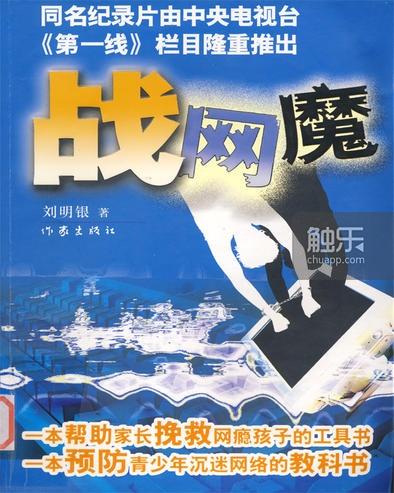
“这一代家长需要成长”
很难说这一切越来越像无望的恋情,还是没有尽头的疲惫战争。邹虹现在会比以前更多地对儿子说“我错了”,“妈妈对不起你”。她“赎罪”的方式是对他更好,效果却南辕北辙,儿子感到的只是母亲过分的殷勤,甚至批判杨永信的行为也像是在表演。她对儿子的这一反馈感到尤其伤心,怎么能说一个母亲发自本能的、高尚的爱的动机是“殷勤”呢?邹虹想到放弃,“他的要求,超出我的能力了。”她意识不到冲突来源并非她对他不够好,也感知不到殷勤令儿子难堪。儿子唯一的诉求——“不要再这么强行地干涉我的生活,我们可以像两个平等的成年人一样相处”——她始终未能明白。
前年,她主动要去意大利看他。一天夜里,本来已经睡下的她发现儿子还在打游戏,这违背了她的养生观点。她要求他立刻睡觉,看到他睡她自己才能睡。最后,邹虹拧着儿子的耳朵,揪着他的头发,要他听从。这让王一南想起了成长中的种种,之后相处的日子对他成了煎熬。机场送别时,邹虹眼泪汪汪,依依不舍,儿子王一南却如释重负。他苦闷地思索,什么时候是个头?去年,邹虹又提议去看他,他直接跟她说,你别来了,来也可以,他不提供住处,保持距离。
邹虹有时候催儿子找个女朋友,却不知自己正是他建立亲密关系的障碍。“我能不走我爹的弯路就已经不错了,我千万不能找一个特别强势的。”29岁的王一南至今没谈过恋爱。他异常谨慎,顾虑重重,踌躇不前。他曾对一个女孩有好感,但当女孩出现数落他、教训他的语气时,“像我妈附身了”,他告诉自己, “带这样的态度,人再好,也跟我没缘分。太危险了。”
就像这一代的大多数父母一样,她已经无力追赶见多识广的新一代的脚步,但仍不放弃,求知若渴,脚步踉跄。王一南在意大利学习艺术专业,策划在夏天带一个儿童艺术旅游团,参观书展。邹虹提出带着她认识的一位摄影师给儿子服务,给王一南发去了摄影师的作品——一组PS过的婚纱大片。王一南拒绝了,在朋友圈发了篇短文《从不切实际的云聊真和美》侧面回击邹虹。
如今她能做的只是扎住营盘,稳住阵脚。2016年8月初,又一轮关于临沂网戒中心的报道集中出现在媒体上。她得知“盟友”们有个微信群,王一南、徐浩都在里边。她猜想群里的氛围,受伤的孩子们聚在一起,越聊越受伤。“关注伤害等于又成了一种新的瘾,离不开。”晚上,邹虹打电话给徐浩,一个小时后,徐浩不得不把王一南移出群聊。
王一南说他母亲还在给他营造无菌环境,她一直没变,一直不相信他——一个29岁的成年人——有任何抵抗力。
王一南有几次丧气地说“趁早出家”。“就觉得这个世界这种苦,真的,你不跳出来,没有幸福可言。”如果母亲能变成一个他觉得可爱的人,他们的关系自然会亲密起来。在此之前,他只能尽可能远离。他不觉得自己不孝,“她需要自己成长,这一代家长他们自己需要成长,他们才配收获亲子之间修复的关系。”
邹虹的能量在过去能多么呵护儿子,就在今天令他多疲惫。有时候朋友开玩笑说她像“江姐”。她在保护儿子的事业上信念超强,斗志充沛,不可战胜。王一南不知道怎么让她明白,她自己就是他痛苦之源的一部分。
她也觉得苦,但心甘情愿地熬着。无论儿子当下如何恨她、怨她,她不较劲,都担下来,只想让他把未来的路走好。她叹息着,“这一辈子我一想起来,怎么就这么活着了,怎么就为这件事?”
邹虹这一辈子,始于1957年,那时她是北京的一个教师之家刚出生的女儿。小学时,她被母亲的学生殴打,造成神经性耳聋耳鸣,嘴唇上方留下一道疤。她的青春期伴随重度抑郁,一度想死。后来,她结婚了,对丈夫不太满意。“我妈就老跟我埋汰我爸。(关系)从小就不好。”王一南说。她养猫50年,把猫当孩子,1988年,她有了自己的孩子,感到幸福。把婴儿王一南抱回家放在床上,她跟一旁好奇的小猫说,这是她儿子,千万不许挠他。2008年,大年夜,她把儿子送进了网戒中心。这是她自己的真实的故事,但她没有兴趣讲太多。她愿意讲的总是受辱母亲或者残疾演说家尼克·胡哲之类的励志故事。在自己的真实故事里,短暂地卸下战斗盔甲的邹虹,显得苍老、疲惫,“离不开,扯不断,还看不到头绪,没完没了。”
不过,邹虹很快回过神来。她对将来不无忧虑——生活里陷阱太多了。沉浸在自己的强大信念中,她像跟自己鼓劲似地说道,“所以我得时刻准备着。”

为保护受访者,邹虹、徐浩为化名,王一南坚持实名,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登录触乐账号
请登录后发表评论、没有账号请注册或游客评论
使用社交账号登录
作为游客留言
请登录或注册,更顺畅地进行交流
使用社交账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