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是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但“关注孤独症”不应仅限于4月2日一天。就像很多人说的,这应该是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从3月29日开始,我和我的同事窦老师在朝阳公园里待了3天。我们受邀去采访一次Game Jam,参与者都是国内颇有名气的独立游戏开发团队。他们之中大部分人住在北京,少部分从天津赶来——以现在的条件,从天津到北京的时间并不比从石景山到团结湖更久。
我们跟着这些独立游戏开发者一起度过了48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要为孤独症人群以及想要了解孤独症的大众做出游戏,而我们要记录下这个过程,以及那些在游戏之外的故事。
孤独症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主题,所有人在面对它时都显得小心翼翼。我们接触到了包括主办方、游戏开发者、孤独症儿童、家长、支援中心负责人、老师、志愿者在内的许多人,有些被写进了文章里,有些没有,还有些人主动要求“不要写到我”。我不知道读者们看过文章之后能够感受到什么,比起“思考”,只要你们能够“看到”,就已经很好了。

在阿火做完介绍孤独症的讲座之后,人们谈论的东西很杂,有和孤独症相关的,也有和孤独症完全没关系的。有人问阿火,“你对儿童心理教育有什么建议”,她只能回答,“我不是做这一块的,不能乱说”。
一位开发者说他以前看过一个视频,里面说“所有人在7岁之前都是个移动硬盘”,学习其实是个传输的过程。他由此提问:“那些孤独症的孩子,是不是相当于传输不太好,别人是USB 2.0,他们是1.0或者3.0,总之就是互相对不上?”
另一位开发者一直在确认:“孤独症人群真的需要‘治疗’吗?假如他们不想和人交流,但我们又强迫他们去社交,岂不是让他们很痛苦?”
更多的人尝试做了阿火提到的“孤独症谱系障碍量表”,不少人的分数让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看上去沉默寡言的,可能只有10多分,蹦蹦跳跳、特别开朗的,居然得了20多分。”人们交头接耳——在这项测试中得分越高的越具有孤独症特质,得分达到35分以上建议“去医院获得正确的诊断和指导”。
一位羞涩的程序员得到34分,是全场最高,仅差1分就要“建议去医院获得正确诊断和指导”。这很难不让人联想起“59分和60分有什么区别”一类的话题,但随后,人们开始讨论、工作,分数就这样被忘在了脑后。
我在活动现场遇到了不少家长,他们花不了太多时间和我聊天,全部精力几乎都要集中在孩子身上。
孤独症孩子大部分都是男孩,贴身照顾他们的大多是妈妈,有时还要加上阿姨,在我能看到的地方,只有一个孩子是由爸爸带来的。活动安排在星期六,我不知道其他爸爸都去哪儿了。
小龙的妈妈是那种会让你觉得很好相处的人。开朗、热情,和谁都能聊到一块儿去,她的性格多多少少也遗传给了儿子。小龙属于智力障碍,许多人对这类人群的偏见和歧视还更甚于孤独症,但小龙从来不怕生人,和我聊天时,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
她一直强调儿子“情商很高”,并且和我分享了许多小龙与《西游记》的故事。除了文章里写过的,还有让她印象极深、极为吃惊的一次:她带小龙出门旅游,在一座寺庙里,小龙长时间盯着佛殿里挂着的画发呆。她去问时,他开始给她详细解说画上的内容,哪个是观音,哪个是文殊,哪个又是普贤……他说,自己是从形象和坐骑上分辨的,《西游记》里都写了。
小龙最喜欢的《西游记》角色是猪八戒,这让我一度怀疑他属猪,但其实他属牛。“他可能觉得自己上辈子是猪八戒,”妈妈笑着摸摸小龙的头,“这辈子呢,这辈子他是我儿子。”
不少家长对我说,手机和Pad对孩子们很有帮助。“把手机拿给他们,不用学,自己戳一戳就会了。”一位家长说。她的儿子也玩过不少手机游戏,可惜她一个也记不起来。
游戏开发者们也在思考人工智能会给孤独症人群带来怎样的变化——假如真的像《底特律》一样,人工智能可以24小时全方位照顾人类的日常生活,那么被照顾的“人类”是否具备与其他人沟通的能力,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
“再说下去快要变成伦理问题了。”一位开发者说。他想了好一会儿,最终只是摇摇头。
阿火对我说了另一个与技术有关的细节:“现在很多医疗设备的技术水平甚至远远落后于游戏,一些需要穿戴的设备还需要使用者把头发全部剃光才行。”她认为,将来医疗设备技术提升,必然会对配套软件有所需求,游戏或许也可以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3月30日,我们特地采访了温洪女士,她是康纳洲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主席,这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NGO),由海淀区残联主管,是中国精协孤独症委员会组织部分家长联合发起创立的综合性孤独症服务平台。活动中表演节目的孩子们就来自这家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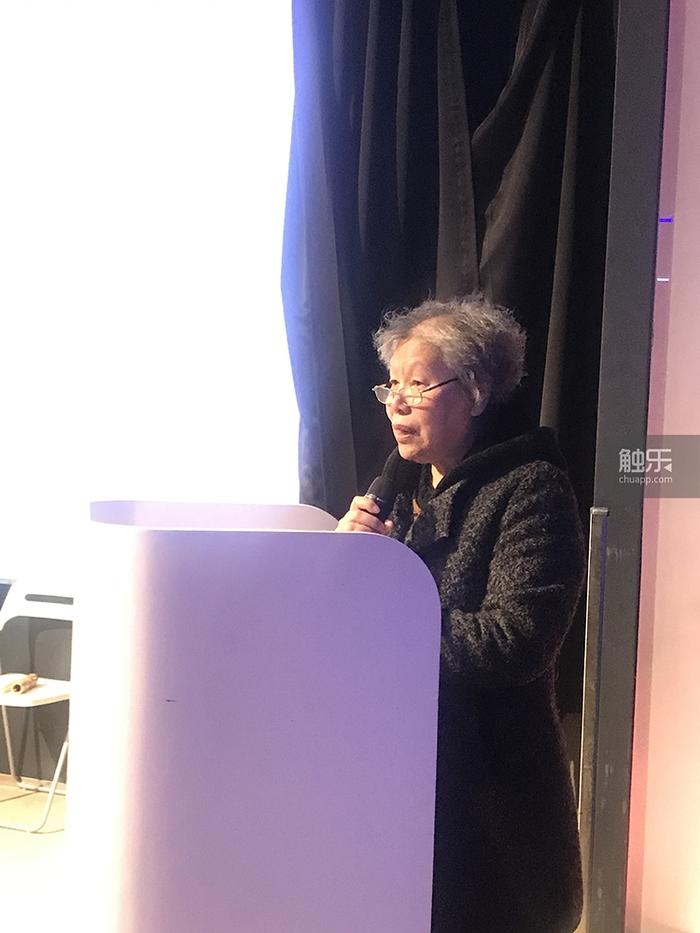
目前固定在康纳洲接受教育和训练的孩子大概有150个,有的是北京本地家庭,还有的来自外地。康纳洲本身不接纳住宿,孩子们白天来,晚上走,假如有外地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他们还需要承担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康纳洲的“康复训练中心”位于五道口,离它最近的小区,50平方米左右的一居室月租金都在8000元以上。
温女士对此也无能为力。康纳洲没有政府专项资金支持,运营并不轻松。“大部分民办的这种(弱势群体帮扶机构)生存起来都是有困难的。”她说。
温女士并不了解游戏,这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谈到让大众了解孤独症知识和人群,她脱口而出的是六七部电影的名字——《海洋天堂》《自闭历程》《马拉松》《我的名字叫可汗》《玛丽与马克思》《雨人》《与光同行》……她对这些电影的情节无比熟悉。
得知有一批游戏开发者正在以孤独症为主题制作游戏,她显得有些迷茫。“(游戏)反正都是快餐,玩过关了,来不及思考,没有人在玩游戏的时候还思考。”
我们向她介绍了一些游戏常识,比如互动性,比如功能性,还有几个成功的游戏作品。她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但始终担心人们会对孤独症人群产生刻板印象——提问时,我们说Game Jam“想尝试为孤独症患者做一些事情”,她立刻纠正“不能这样称呼”。她始终叫他们“孩子”。
在听说“游戏在年轻人之中认可度很高,可以通过游戏向更多年轻人传递孤独症知识”时,温女士认为“这个思路很好”,但她们自己既不懂游戏,又从来没往这个方向想过,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对于游戏开发者,她希望他们能再多接触孩子们一些。
“要不你们先去哪个机构当两天志愿者吧,”她说,“也体会体会孩子们的生活。”

说真的,我始终不确定Game Jam能在孤独症儿童和他们身边的家长、老师、志愿者中造成多少影响,我也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是不是了解、关心弱势群体过程中的常态,但就像很多人说的,这只是个开始。假如孤独症孩子们——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所需要的了解和关爱是100,那么我们或许只做到了1,不过1总比0要好。
登录触乐账号
请登录后发表评论、没有账号请注册
使用社交账号登录
绑定手机号
根据相关规定,无法对未认证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跟帖评论服务,请尽快绑定手机号完成认证。
共有4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