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高考结束、那段夏日噩梦结束,我从未强烈地坚持过某些事情,或者坚守过某种原则。我会长大,放弃很多事情。但我始终会记得自己用绝对的执着,取得过两次可疑的胜利……”
上高中之后,父亲一直有一种危机感。他常常睡不着觉,在凌晨时的黑暗客厅里游走,时不时陷在沙发上,盯着货车灯光拉出的长阴影在墙上掠过,为我的将来忧心忡忡。有时候他会走进卧室,摇醒我,说一些可恨的话。
他似乎相信我没有在好好看书。即使好好看书,书里面也是别有洞天。即使我没有在《三年模拟》里夹藏史蒂芬·金的小说或者《男人装》杂志,也可能是在神游艾泽拉斯。
即使我没有神游艾泽拉斯,而是竭力学习,也可能学不进去。
即使我学进去了,也可能进考场忘带学生证。即使带着学生证坐在了椅子上,也可能中途肚子疼腹泻,或者填错答案,或者字迹潦草,或者感染埃博拉病毒暴毙。
即使上述一切都没有发生,最后的成绩也可能不尽如人意,我考不上好大学,只能在某个偏远地区的陷阱专业里虚度岁月,出来后对知识和教育的价值产生深深的质疑。
他问我,这该怎么办?
可是在2012年的那个夏天,他完全是杞人忧天。走出考场,我几乎处于一种禅定的状态,回到家,我看着吊扇非常安心。
成绩短信来到后,我的胸口热热的,好像阳光下的一块大理石。父亲看了一眼分数,没有说话,他把家里电脑机箱的钥匙交给了我,允许我时隔三年玩玩游戏,然后他就去睡觉了。他的心安了,所有担忧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不过,他睡得太快了,还有一件事情没来得及担心。
那就是,即使我考上一流大学的热门专业,我也可能闯了什么祸,而不去学校报到呀。如果生活真地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绝对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正放暑假的高中毕业生,他们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那是狗都要变成狼的夏天。
我的确让自己失望了,当时,我容光焕发地来到自己卧室,打开锁着戴尔台式机机箱的柜子,抚摸着机器黑色的塑料表面,右侧壳子上还有一个浅浅的脚印,那是我的脚印。
“三年不见了,想我吗?”我叹了一口气。

如果戴尔机箱有灵魂,她会带着巨大的轻蔑看着我。三年前,初中毕业,我拿它玩《魔兽世界》和《DotA》,有时候父亲冲我发脾气,我就会把气撒在它身上,很用力地朝着机箱踹去。
如今,它的噩梦又要开始了。
摁下电源按钮,机箱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开始发出一种低沉的、连续的轰鸣,轰鸣中不断加入新的声音,好像机箱本身的各个构件在逐一苏醒。最后,那种轰鸣几乎变成了啸叫,有点可怕,于是我抬起脚尖踢了它一脚,就像拍打电视机的盒盖。
机箱狂吼暴跳起来,我又踢了第二脚,于是它呜咽一声,安静了。
“肖明,你不要玩太久啊,马上要吃饭了。”母亲围着围裙站在门口对我说,那眼神绝望得就像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质正在努力处理自己的斯德哥尔摩情绪。
“放心吧,我对游戏已经没有兴趣了。”我说。
我弯下腰解开缠绕的线团,把插头一一插进插座。
我接上蒙了一层灰的显示器,接上鼠标、键盘、Xbox手柄。
开机后,桌面还是老样子,《魔兽争霸3》巫妖王的壁纸。上面放着几款老游戏,《反恐精英》《实况足球》《新浪游戏大厅》《魔兽争霸3》《仙剑奇侠传四》……

12点整,不待母亲喊,我悠闲安适地走进客厅。母亲端着一锅鸡汤愣在厨房门口,表情看上去有些滑稽。
“咦。今天这么晚开饭呀?”我装模作样,笑嘻嘻地走上前去,接走那锅香气四溢的汤。
“你就出来了?”
“是啊,出来了。”
“真出来了?”
“还能有假?”
“我还以为你一时半会出不来呢。”
“不会的,我出来了。”
“不会又进去吧?”
“不会的。”
“不会端着碗回去吃吧?”
“不在饭桌上吃饭的玩意儿,也配称作大学生吗?”
“不配,猪都还有食槽哩!”
“畜生才会在家里离开饭桌吃饭!”
“儿子长大了。”
吃完饭,洗好碗,我又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卧室。我决定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在显示屏前面,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像一个戒酒很多年的酒鬼在自己眼前摇晃一杯马提尼,像一个曾经被咬出了豹纹的大橘猫,如今在小别墅的围墙上垂下尾巴逗弄那只满身尘埃,双眼发红的土狗。
我挑衅般地看着显示器,对自己无欲无求的状态相当满意。
你来呀,你来呀,你咬我呀!
是的,我就这么看着,一点也不想玩儿。我就贴着悬崖走,绝不摔下去。
直到那个陌生图标突然出现在电脑一角,文件名是“黑色远征”。
我依稀记得那是制作得非常粗糙的图标,像素点阵画出一个灰红相间的东西,看了良久,才觉得那应该是一个披着红色罩袍的骑士。
我当时揉了揉眼睛,图标还在,我不记得自己玩过这款游戏。图标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
是不是爸爸下载的?不太可能。
奇怪,真是奇怪,病毒?
这时候是下午一点,太阳烤焦了窗台外一树的知了,街上的汽车都晒得溶解在地,万物一片寂静,我打开360管家,把图标原地址的所有文件都扫了一遍,没有病毒。
仔细看看相关文件,我判断这是某种游戏软件。
试试吧,点开。我想象不出有任何方法不去点一点。我为什么要去点它?因为它就在那里。自从出现了桌面应用程序,或早或晚,我们都会点开不该点开的东西,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然后建立对自己的清晰认识,从此不再自命清高。
屏幕一黑,没有商标出现,什么都没有,就那么黑了半分钟。快捷键操作也跳不出桌面,我困惑得都打算去拔电源了。
突然,游戏手柄震动了一下,我下意识地把它抓起来,手指接触手柄的瞬间。屏幕亮了起来,开始一页一页快速地展示各类似乎是说明性的文字。由于全部是日文,我只能勉强看懂其中的汉字。
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光”“噪音”“闪烁”“污染”“精神”“晕眩”“××障碍症”……一系列令人心生警惕的字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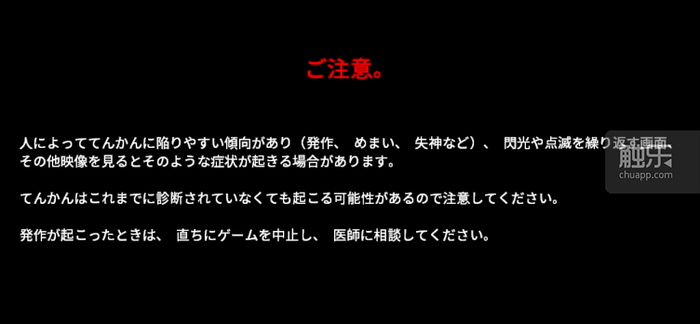
我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存在游戏光污染导致癫痫症等情况发生,很多日产游戏都有类似警告。即使看不懂全文,也能大概理解意思。作为一个老玩家,我以前已多次看过类似的,翻译成简体中文的警告。
但是,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每一页都这么长……一页,又是一页,又是一页……全都是看不懂的平假名、片假名,密密麻麻地挤在高对比度的画面里,好像一堆黑暗中惨白刺眼的骨头。
冗长的警告信息播完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超越我的理解。我只记得先是有一道持续,低沉的白噪音播放出来,紧接着画面开始有规律地闪烁,时短时长,时断时续,假若我学过摩斯电码,一定以为有人在通过频闪传达某种信息。
闪烁持续了多久,我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整个过程中我一动不动,好像怔住了,沉浸于没有思绪的平静状态。等闪光结束后,自然而然地,我的手抓住了手柄,并且开始流汗。
我是一个战士,出现在一个诡异的,荒无人烟的世界里,一个孤孤零零的女人站在身后,升起了一簇篝火,在那里望着我,我记得,她有一头火红的长发,或者是因为画面太不清晰了,脸孔显得模糊不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一定很美。
她从斗篷里拿出一把直剑,递给我,然后沉默地指了指前方,需要做的事不言自明,我往小路走去,离开了火焰照耀的温暖之处。
黑暗之中,只有幽魂、疯掉的战士、畸形的妖怪。
每当我的战士死去,都会重新在篝火旁醒来。

我的脑袋里开始出现一些控制不住的念头,作为这些念头的主人,我却无法予以理解。那天午后,母亲几次来到房间,想对我说些什么,什么呢?不记得了。后来的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复述给我的。
比如,他们告诉我,当时我怎么都不肯起身去吃晚饭,父亲仍在惊喜之中,决定惯着我,把食物拿进了房间,可我依然不吃,直到他们觉得有些恐怖,开始训斥起来,我就像狗一样把脸埋进汤碗里。那时,我还留着长及睫毛的刘海,脏污油腻的发丝打进我眼睛,让我清醒了一阵子,奇怪的是,我连自己清醒时的想法也记不清楚了。
他们告诉我,我的确有好几次关掉了屏幕,在客厅里坐立不安地走了一阵子,和我说话,我也会回两句,但只有“嗯”“啊”,没有惯常的俏皮话。我总是坐回电脑前,继续打开游戏。父亲说我刚刚考完试,也许只是压力太大了,需要宣泄。
可是这种宣泄,多么像脚被一块玻璃片割伤后,拿拳头去砸地宣泄。
母亲说,她拿着湿毛巾来给我擦脸,因为我当时双眼发直,咬牙切齿,表情十分可怕。她记得画面里有一个盔甲破损的战士,在灰色的天空下挥舞着长剑,和一群泥浆一样可怕、模糊的黑色怪物战斗。整个世界都黯淡、模糊、充满锯齿。她为我打开了台灯。
我怀疑自己玩了一整个通宵,是否如此我也不清楚。母亲说,第二天早上她醒来,发现我趴在桌上睡觉,手里仍然抓着手柄,显示器亮着。那个战士坐在篝火旁,把脑袋靠在红发女人的肩膀上。火焰驱散了浓雾般的黑夜。她问我是否睡觉了,我说“嗯”。
假期第二天,因为生意上的事情,父母不得不去长沙出差。据说他们离开的时候嘱咐了一大堆东西,但显然我没有听进去,他们忧心忡忡,叫了表哥有空来看我,可是他们没把钥匙给他。
某个凌晨,我的意识相对清醒,当时我打开门去拿饮料,看见客厅中央的地板上有一条奇怪的,暗暗的长影,越是走近,越觉得恶臭无比。
我打开灯,看见一长滩湿乎乎的粪便。是贼吗?我不是一个人在屋里吗?我摇了摇昏昏涨涨的脑袋,转身回卧室拿起烟灰缸,仔仔细细地查看了每个房间。最后我摸了摸自己的裤子,又湿又黏。我脱下了脏透了的裤子、内裤,发了一会儿呆,又晃荡着生殖器跑到冰箱那里,拿出一颗番茄咬了起来。
三天后,父母回到了家——当然,我并不知道。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心情。想象一下你拖着行李箱来到家里,看到地板上的褐色脏迹、桌上放着被撕下一口的生肉、各种瓶瓶罐罐摔在四处,而你刚刚考上不错大学的宝贝儿子正光着屁股玩游戏,看上去三天没有好好睡觉。
他们肯定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说服我放下手柄。父亲的膝盖朝下的一块位置,至今还有一块浅粉色的伤疤,而我卧室窗台的一块窗帘与屋里的其他窗帘不是一个款式,还有那个碎掉的花瓶。
细节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没敢说。不过,我记得父亲要去拔电源的时候,我掐住他的脖子,把他往一面墙上摁过去,他后脑勺撞到的墙面上至今还有一个浅坑,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他当时闭着眼睛,很虚弱地说:“儿子,疼,我疼。”
直到很多年后,深入了解我的人总会反复提到这段时间我脑袋里真正发生的事情,我的第一任女友是个民间心理学爱好者,她通过催眠、谈话、冥想的方式助我回忆。
我能回忆到的,就是操纵那个战士在黑暗世界里砍杀、前进,每一次都走得更远,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他合二为一,我记得自己乐此不彼地杀死眼前的怪物,那些泥巴一样污秽的东西,它们有时与黑暗的背景融为一体,于是看上去我就像一个盲人,朝着长满利齿的黑夜挥舞刀剑。

除了那些数不尽的杂鱼,还有一些可怕的怪物,它们一次次地杀死我。巨大的龙、成群的老鼠、挥舞着大刀的骷髅巨人、孤独的剑客……它们背后一定有着某种故事,可是我完全无法理解。
我记得自己带着满身的血迹,走向一条条弯弯绕绕的歧路,最终回到篝火旁——那是整个世界的中心。
经历惨烈的战斗后,不论输赢,那个守着篝火的姑娘总会起身迎接我,会用一朵洁白的花拂过我身上的裂口。然后她会让我靠着她的肩膀——我真的能回忆起那种温热——在篝火旁休息一会儿,想到那个场景,我的眼角就会不由自主地湿润。
我不知道你。我的青春期没有恋爱,也没有特别好的朋友。我那时看起来很丑,不是个阳光的人,而且我讨厌我的舍友。高考结束那一天,他们邀请我去聚会,我没去。
所以当我有一天回到篝火旁,看见火焰仅仅余下一点星火,一个高大的、裹着浓雾的骑士,拿着匕首插进女人的腹部时,我——我和我操纵的战士已经你我不分了——感到强烈的愤怒。母亲回忆说,那是我玩游戏第五天的事情,当时我表现得非常暴力,她一直在哭,父亲急得到处打电话。
那个骑士看见了我,便放开女人。
踏着诡异、碎乱、不阴不阳的步伐,他友善地挥着手,一点点靠近。在三剑之距外摘下了头盔,露出一张浮肿的东方人面孔,洗漱的黑色短发上有一撮杂毛,戴着一副用胶带粘好的中世纪风格的眼镜,下巴上有一小捧胡子。
他从屏幕里斜眼看向我,露出一副浅浅的笑容。
他伸出左手,我走向前去,迟疑了。骑士的另一只手则掏出短剑,插入了我的肾脏。
我连忙后跳,回血,并掏出直剑刺去。
那个阴险小人却掉头就跑。
我气急了,气得想要撕了他。我从未对一个真实的人产生那样的深仇大恨,但在连续玩了五天游戏后,我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我要抓住这个家伙,我要揍死他!
我的战士不断追去,脚下突然腾空,掉入坑洞,坑洞里都是尖刺……我在几乎燃尽的篝火旁复活,身上的血肉由于无数次的死亡而剥落,变成一具骷髅,但是我仍然拿起剑,朝着骑士奔逃的方向追去。

他和所有那些发狂的妖魔不同,他,他好像一个活生生的,带着恶意的人,每次他刺一剑,那一剑都朝着我的要害奔去。
在被他连续杀死十三次后,母亲记得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当时轻轻说:“打完这个怪……我就不玩了。”
后来我几乎陷入了彻底的失神状态,以下这些事情都是父母说的,一个星期过去后,父母一起浏览网上各种可以求助的信息。
他们翻找了好长一阵子,一个奇怪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拿到父亲的电话,给他打电话,加了QQ,签名滑稽可笑——“黄大师:手机、电子辞典、台式机、笔记本电脑、电子表、电视、收音机等维修。兼治网瘾。老实本分、价格公道。”
母亲回忆说,那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叉着腰站在我家客厅里。他嘴里叼着一根牙签,在肥厚红润的嘴唇里滚来滚去,身上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牛仔吊带工装,一个肩带已经磨损,散发着机油和青草的味道。
“电脑的问题?”他一边问,一边麻利地拿出工具箱,把防静电除尘布、螺丝、起子、摆在饭桌上。“等一下,情况比你想的要复杂。”父亲急忙说。
男子大喜,搓了搓手,又从手提箱里拿出一块替换用的CPU,放在嘴边,吹走一层积灰。“……你还是进来看看吧。”
“这有什么,很简单啊。”黄大师望着我,惊恐地说。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很简单啊。”黄大师拿来一款又粗又硬的黄绳子,一根保安棍插在腰间。
“不准动粗!”
“喔,那就让他彻底睡过去。”黄大师手上拿出涂满昏睡药剂的布。
“安全吗,不会有什么后果吧?”父亲困惑地问。
“没有!”黄大师真诚地望着两人。
父亲和母亲犹豫了一下。“要不,试试?”
黄大师突然展开棉布,一手抓住我的肩膀,一手拿白布盖住我的嘴唇。我毫无抗拒的能力,我感到呼吸先是急促,而后和缓,渐渐的,大脑有一部分麻痹了下来,我的思绪变得更加模糊不清,直到左眼止不住合下。
我进入了半脑睡眠的状态,就是像鱼、像鸟一样,只用一半脑袋睡觉,另一半脑袋继续维持身体的运动,这是真事儿,我没有编。

它们在水里,在空中半梦半醒,仍然能挥动翅膀,甩动鱼尾。
不知怎么回事,我找回了这一人类在漫长进化中丢弃的艺能。
我闭着一只眼睛,继续用磨破的手指,机械地摁着手柄——当然,同时我浑然不觉。
“打完这个怪我就去吃饭……”我用气若游丝的声音说。
“啊!”黄大师以拳击掌,恍然大悟状。
“怎么又简单了?”
“对啊,简单,你让他打完这个怪就好了。”
父亲气得发抖,揪住黄大师的衣领摇来摇去。
“催眠时人不说谎,他们说到做到!交给我吧,我去一会儿,速速就来!”黄大师一把推开父亲。
二十分钟后。黄大师带着一个日本人走了进来,黄黄的头发,双手插兜,睡眼朦胧。“介绍一下,这是梅原小吾先生,国际友人,他会帮你们的儿子打掉这个怪。”
可是他们根本无法从我手里把控制器抢下来。
“我有办法。”黄大师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扔到地上,从里面拿出一块稀奇古怪的小装置——两块银色的,厚度约为四厘米的不规则金属盘,从盘的一端伸出一些细小的针头,另一端通过一条缆线和另一个金属盘相连。
黄大师从身后勒住我的脖子,使我脑袋后仰,抓住一个金属盘,把有针头的一边刺入我的额头,鲜血立刻从我前额里涌出,从眼角流了出来,好在大脑内部没有痛觉感受器,所以倒不是很痛。
母亲吓得差点报警,最后哭着端来一盆热水给我擦拭脸上的血迹。
梅原小吾则满不在乎地拿起另一个金属盘插进自己的脑袋里。然后坐在我的侧面。我能闻见他嘴里的那股讨厌的烟味。

突然,我感觉手指不再听从自己的指挥——梅原小吾接管我两条手臂的控制权。原本疲惫、迟钝的手指突然开始迅捷地跳动,遥感、扳机、按键被拨弄敲打,发出老账房拨算盘一般的声音。
我看见手柄上正在操作的六根手指突然出现了重影,分成了十二根,接着又是二十四根。
两小时后,我的手指开始滴血。梅原小吾扯下额头的金属盘,气哼哼地站起来,点起一根烟,望着窗外的风景沉默了好久——那里有一群孩子在绿茵地上跳操。
“ちくしょう、すげえ難しい。”他说。后来我翻译过他的话,意思是:“妈的,好难。”
在浑然不觉中,整个家庭的运作方式围绕我开始重组,各种各样的人接二连三地跨入家门。
为了让我维持营养,一个护士开始给我打葡萄糖吊瓶。
为了正常排泄,医生给我做了一个临时的人造结肠瘘袋。
母亲一天三次替我擦洗身体,按摩颈椎。
梅原小吾不断邀请各国友人来脑控我的手指,帮我打怪,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而且都抱怨这个游戏Not Fair。因为,在经历无数次的死亡之后,我的战士已形同尸骸,守护篝火的女人也渐渐虚弱,无力为我疗伤。
我的手里拿着一把断剑,仅剩剑柄和剑柄上端的一部分,无论是挥砍还是闪避都十分吃力,只能像疯子一样胡乱甩动武器。而对手,那个阴诈的骑士始终强大,不知疲倦。
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了夏天的中旬,我始终没有打完那个怪。我的健康状况与日俱下。但即使是如此虚弱的身体,当他们过来争抢手柄,试图制服我的时候,还是能展现出向死的决心和力气。
他们只能等我虚弱到无法睁开眼睛。到了那时,我可能会住院,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终于,我可能无法入学报到这个判断,压垮了父亲。
有一天凌晨,所有人都走了,累得瘫软的梅原小吾在我床上呼呼大睡,而我趴在桌上,半睁着眼睛睡觉,在迷雾中寻找着那个骑士的身影。
父亲在客厅里,幽灵一般游走,他的状况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突然,在骑士从雾中出现的瞬间,我意识到父亲站在了我的身侧,满脸的疲惫,眼睛里都是血丝,他左手伸出,放在我的手柄上,扯了一下,我纹丝不动,死死抓住。
父亲没有松开,他的右手也伸过来,像拔河一样和我较起了劲。我咬牙切齿,一点也不松劲。母亲也过来加入了竞争,六只虚弱无力的手裹缠在小小的手柄上。
父亲的脸涨得通红,开始狂吼乱叫。让我产生了些微的清醒。发怒的父亲,跟个猴子一样上蹿下跳,尖声大叫,那模样几乎有点滑稽。
我继承了他的脾气,我和他斗争的结果,有时就看谁发脾气发得更快。慢一步的那个人总是气上不来。我输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长期紧绷的神经,让我只觉得搞笑,提不起那口气。
手柄脱手的瞬间,我却感到一丝悲凉,因为我在瞬间意识到自己彻底失败了。虽然原则上我有无数次尝试挑战的机会,但沉没的成本已经堆积得像哈尔滨的雪地一样厚实。
我没法拯救那个红头发的女人和她黑暗的世界了,我为此感到真心实意的遗憾。
可事情并没有结束。
父亲抓走了手柄,可是在某种愤怒的眩晕中,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胜利的事实,而是寻求更深的宣泄。他抓着那沾满血迹、汗液、油光发亮的手柄,正面朝下,恶狠狠地往桌角砸去。抓着手柄的手在空中来回挥舞。
哐当!砰!丁零当啷!坚固的手柄在黑夜里飞舞,一下又一下俯冲向桌角。
母亲向后退缩,我仿佛看到了幻象——我操控的发狂的战士跳出了显示屏,在眼前挥舞折断的直剑,向那台气喘如牛、灼热发烫的电脑怪物袭击。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那么盯着屏幕,瞳孔越来越大。我听见骑士在惨叫,脚步碎乱,身体失衡,狂野的断剑一下又一下刺进他的身体。
猝不及防的,梅原小吾在身后拼命鼓掌,高声叫好,他的脖子红通通的,好像被人勒紧了。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昏倒在地。
……
……
……
“然后呢?”女友问。
我躺在沙发上,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父亲打死了那个怪,也砸烂了手柄和电脑机箱,等我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那台电脑已经进了废品收购站。
梅原小吾倒是颇有先见之明,从父亲的打砸中抢救了硬盘,不过读取之后发现硬盘里什么都有,却偏偏没有那款奇怪的游戏,它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所以你从来不知道游戏的结局?那个女人的结局?”
我犹豫了一下,说,嗯。
“你觉得那到底是什么情况?黑客攻击?这种具有催眠能力的软件,简直可以作为武器,也许是国外阴谋机构的实验……比如FBI,毕竟,美国鬼子坏透了。”
“哈哈……”
“我很欣慰,你玩游戏节制多了,那种状况太可怕了。”女友认真地说。
“嗯,不过,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觉得,要是我对现实中的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情,还有那样的执着就好了……也许吧。”
“也还是很可怕,凡事不能太偏执。”
自从高考结束、那段夏日噩梦结束,我从未强烈地坚持过某些事情,或者坚守过某种原则。我会长大,放弃很多事情。
但我始终会记得自己用绝对的执着,取得过两次可疑的胜利——两次胜利背后的代价都值得质疑,两次胜利也都离不开他人倾尽全力的帮助和关怀。
高考的胜利让我不至于面对一些窘迫的处境。而那款游戏的胜利……
就当我疯了吧,有时,我写作到夜深时,有时会看到电脑突然屏幕一闪。屏幕里,一个红头发的女人,会在月光笼罩的草原上,顶着繁星,烤着篝火,朝我露出半是感激、半是愧疚的微笑。

* 本文系作者投稿,不代表触乐网站观点。
登录触乐账号
请登录后发表评论、没有账号请注册
绑定手机号
根据相关规定,无法对未认证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跟帖评论服务,请尽快绑定手机号完成认证。
共有0条评论